我在國務院與財政部的工作,讓我近距離見證了美國如何把經濟轉化成武器。這不是一夜之間的發明,而是長達數十年的積累與磨練。冷戰後的全球化,讓世界經濟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密。美國正好站在這個網路的中樞──「美元」是國際結算的基礎貨幣,紐約和倫敦是全球資本流動的心臟,先進技術多半源自美國或由它主導的體系。這些本來是經濟繁榮的基石,但在戰略思維裡,它們同樣是鎖喉點。
911 之後,恐怖主義威脅迫使我們重新檢視金融系統的角色。財政部成立了「恐怖主義與金融情報辦公室」(TFI),開始把反恐資金追蹤與經濟制裁結合起來。這套模式後來被應用到伊朗:透過凍結資產、將銀行逐出 SWIFT、禁止美元交易,我們讓伊朗的對外貿易幾乎停擺,逼它回到談判桌。
全球化將美元催化成武器
在這些行動中,我們學到一件事,當你的對手必須經過你的系統才能與世界做生意,你就握有主動權。制裁的精髓,不在於你能封鎖多少,而在於對方為了避開封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隨著時間推進,我們的工具箱越來越精密。金融制裁、出口管制、投資禁令,不再是孤立的措施,而是可以疊加、互補的系統武器。每一種工具都針對不同的脆弱點:
- 金融制裁 切斷資金流與結算系統。
- 出口管制 阻止關鍵零組件、技術和軟體進入對方的產業鏈。
- 投資禁令 限制資本、專業與技術流向敏感領域。
美國對中國開的第一槍:外科手術式打擊策略
當中國崛起成為戰略競爭對手時,這套武器庫自然被調轉方向。美國對中國的第一波重大經濟制裁,並不是全面封鎖,而是針對特定企業的「外科手術式打擊」。
中興通訊是其中一個關鍵案例。美國商務部指控它違反對伊朗與北韓的出口禁令,於是禁止任何使用美國技術的企業向它供貨。這不僅切斷了零組件的來源,還斷了它對關鍵軟體的更新。短短數週,中興幾乎陷入癱瘓,直到簽署高額罰款與監管協議才獲得喘息。
華為的情況更複雜。它不只是電信設備供應商,更是中國在 5G 與通訊技術上的旗艦企業。我們先將它列入「實體清單」,要求任何向華為出口的美國公司都必須申請許可,接著擴大到《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即便晶片是在海外製造,只要使用了美國的設計軟體、設備或技術,也必須遵守美國的管制。這等於把全球晶片供應鏈都納入制裁範圍。
對華為的封鎖,不僅削弱了它的高端產品線,也向中國整個半導體產業釋放了訊號:先進製造環節依然受制於美國主導的生態。這就是經濟作戰的另一層意圖:不只打擊當下的對手,還要延緩它在關鍵領域的追趕速度。
這些手段的有效性,來自幾個現實:
- 美元的中心地位:任何跨境交易幾乎都會經過美元結算,美國法院與監管機構因此對全球金融有實質管轄力。
- 技術生態的依存:從半導體設計到製造設備,美國及其盟友掌握核心節點。
- 市場規模與盟友網路:美國不必單打獨鬥,可以透過與歐盟、日本、韓國、台灣的協調,擴大制裁的覆蓋面。
制裁並非沒有代價
當然,制裁並非沒有代價。中國加速推進「自主可控」戰略,投入巨額資金發展本土晶片、作業系統與支付系統;同時尋找替代市場與金融通道。這意味著,我們的鎖喉點未來可能不再那麼穩固。
但在當下,美國依然握有絕對優勢。正如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的,經濟作戰不是戰爭的輔助,而是戰爭本身。在與中國的長期競爭裡,制裁與管制將繼續是核心戰術:不必開火,卻能改變對方的行動與選擇。
我常被問:這樣的經濟戰會持續多久?我的答案是,只要全球化仍以美國為中心運轉,這場戰爭就不會結束。因為經濟與安全早已無法分開,而鎖喉點就是新的前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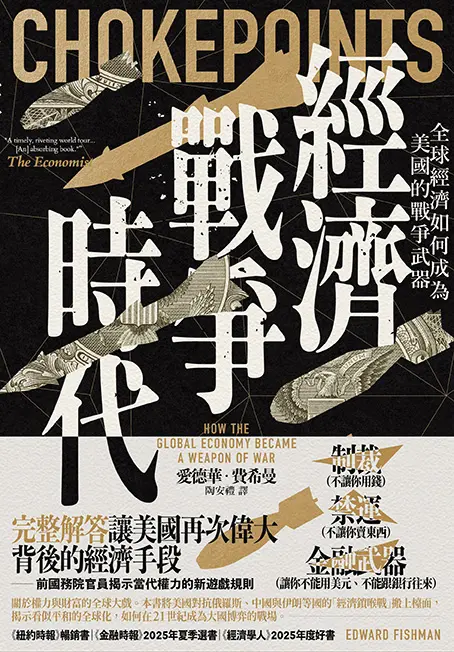
《經濟戰爭時代:全球經濟如何成為美國的戰爭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