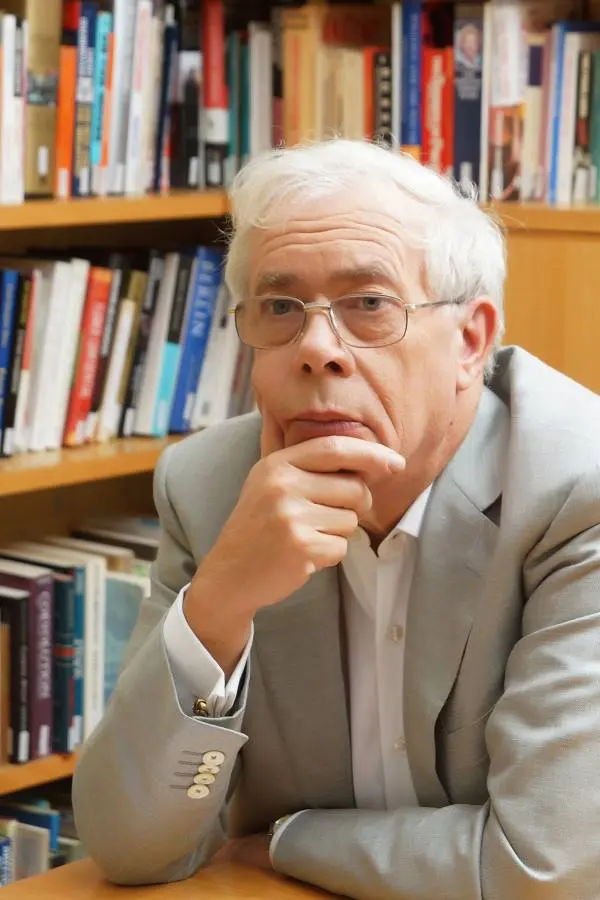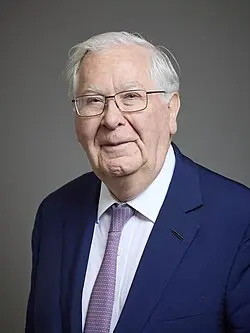《牛津詞典》把風險一詞定義為「不愉快或不好的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也是摩根大通(J.P. Morgan)的董事會、典型的家庭、賽車手或登山者所理解的風險。 風險的一般意義指的是不利事件,而不是有利事件。
風險是不對稱的。我們不會聽到有人說「我有中頭彩的風險」,因為他們並不會把中頭彩視為風險。他們甚至不可能說「我有槓龜的風險」,因為他們其實沒有預期自己中彩券。風險的日常意義是指危及個別家庭或機構的現實期望的不利事件。所以,風險的意義是家庭或機構計劃與期望的產物。風險必然會因人而異。風險對摩根大通的意義,異於對滑翔傘運動員或登山者的意義,也異於想為退休或孩子教育而儲蓄的家庭所想的意義。
很多時候,我們擔心的風險不是對現狀有風險,而是對我們改變現狀的計劃有風險。我們制定商業策略及退休計劃。我們把積蓄拿去投資或從事新規劃,例如度假或建築工程。我們做那些事情時,都對結果有所期望——那些期望是一種敘事形式,而不是機率形式。我們從來沒聽說過「今年度假的價值有七○%的可能性比實際付出的金額多一百英鎊」這種話,我們常聽到的說法是,他們預期今年的假期是有史以來最棒的,或是在假期結束後才說他們大失所望。
參考敘事
我們認為透過「表達實際期望的故事」,即「參考敘事」(reference narrative)的概念來了解對風險的態度才是最好的方法。對摩根大通而言,最重要的參考敘事是銀行持續獲利成長。一家大企業有很多策略可以在其營業領域中實現那個最重要的目標,旗下每個事業單位也有一個相關的參考敘事。有些事業單位的參考敘事可能風險很大,但只要那個事業單位的參考敘事不危及整個組織的參考敘事,公司就有可能會包容那種風險。
家庭同樣也有最高層級的幸福與安全目標,以及許多附屬的敘事——例如買房、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享受舒適的退休生活。對一級方程式賽車的世界冠軍來說,風險可能是阻止他贏得比賽的因素;但是對比較沒那麼優秀的賽車手來說,風險是沒達到一個好看的名次;對觀眾來說,風險可能是賽車在第一個拐彎處偏離車道。登山者面臨的風險是那些阻止他到達頂峰的事件。風險的意義因個人、家庭或機構而異。
在歐巴馬下令海豹突擊隊突襲阿伯塔巴德的那場會議上,有一段參考敘事支配了那場會議。直升機會降落在那個基地,突襲隊衝進大樓。我們假設(但不知道)這裡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賓拉登將在這場突襲中遭到擊斃。無論他是死是活,他都會在美國的羈押下,由飛機運離巴基斯坦。那段參考敘事或多或少描述了實際發生的事情。
但許多事情可能會打亂那種敘事。那次行動可能遇到設備或後勤問題(一九七九年營救德黑蘭人質的行動,就是因為遇到突發問題而失敗)。賓拉登可能不在那個基地裡,因為美國的情報有誤,或突襲時他剛好不在。總統與顧問針對這些風險進行辯論,並討論適當的因應措施。最棘手的問題是,萬一巴基斯坦軍方迅速察覺這次美軍行動並動武回應,美方該如何處理。首要目標是確保參考敘事是穩健且有韌性的。風險管理的關鍵,就是辨識參考敘事是否有穩健又有韌性等特質。
由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參考敘事,不同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評估同樣的風險。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員工所面臨的風險,可能與該公司股東所面臨的風險不同。對一九七○年代抗拒開發小電腦的IBM高管來說,他們的風險在於:個人參考敘事是以公司既有的商業模式為基礎,開發小電腦可能導致他們的個人參考敘事貶值,連帶他們的公司地位與專業也會跟著貶值。
風險是指預測敘事(projected narrative)的發展不如預期,而預測敘事是從現實的預期推估出來的。快樂的父親滿心期待著女兒的婚禮,他心裡想的參考敘事是一切按照計劃順利進行。他知道有很多種風險存在,例如新郎臨陣退縮、傾盆大雨淋濕客人等等。那種評估中隱含著一種風險的衡量——結果可能與預期相差不大,也可能相差很大。該風險的規模也許可以量化,也許無法量化;可能發生在事件之前或之後。但這種詮釋方式跟後來主導計量金融及許多經濟學與決策理論的觀點(亦即風險可以視同結果的波動性)截然不同。
更多金融敘事
經濟學家席勒主張,想了解經濟行為為什麼會出現又大又有破壞性的變化(無論是股市泡沫與崩盤,還是經濟蕭條期間的產出驟減),就得了解情緒的波動。
但席勒對敘事的關注是片面的。他用敘事的概念來解釋世人稱為「風潮」的行為;換句話說,儘管敘事可用來解釋行為,但他認為敘事偏離了「理性」的最適化行為,所以是非理性且情緒化的。套句他的說法,「在一般人之中,敘事往往有些不誠實,帶有操縱性」,「因此經濟敘事所涉及的行為,往往是因為聽到別人說自己做了哪些事情而跟著去做。」
但敘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人類行為的弱點,而是因為我們需要在極端不確定的世界中做決策。的確,在某些金融市場中,敘事有時「不誠實、帶有操縱性」,但一般人是誠實地使用敘事來了解環境,並在極端不確定性下用敘事來指引他們的決策。我們需要一個敘事才能回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些真實事件確實改變了經濟的基本面以後,有感染力的敘事往往會影響金融市場。由於敘事的傳播一定是循序漸進的,隨著後來的人跟風抬轎,最先相信那個敘事的人可能會獲得豐厚的報酬,而且評論者往往誇大了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大家普遍認為,世人容易高估一項新技術短期的影響,而低估其長期的影響。
關於金融泡沫的開創性著作,首推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的《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這本書寫於一八四○年代的鐵路狂熱時期,追溯了早年充滿感染力的金融愚行,從一六三○年代的荷蘭鬱金香狂熱,一直談到一個世紀後的南海泡沫。最近有學者對荷蘭鬱金香狂熱的性質和規模提出質疑,那個風潮看起來似乎特別愚蠢;然而,把那些風潮歸因於妄想,並未點出那些敘事中常見的真理核心。沒有人會懷疑,十八世紀開始的國際貿易成長、十九世紀的鐵路建設,或一九二○年代無線電與商業航空的發展等等,都是讓經濟脫胎換骨的轉型事件。
同樣地,投資者肯定以下的事實也是正確的: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日本製造商的成功,不僅使日本崛起為主要經濟大國,也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廣泛成長的前兆。不過,隨著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這個事實也無法證明日本股票及房地產的價值是合理的。後續十年,在其他的新興市場中,幾乎立即重複了同樣的過度擴張與反應——比方說一九九九年的「新經濟」泡沫,以及歐元上路後,歐陸各地的利率趨同期間。在這些例子中,隨著更現實的情況終於出現,投資者都損失了大量的資金。敘事的崩解是比敘事的傳播更迅速的流程。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融媒體上充斥著鬱金香狂熱引發泡沫以來最薄弱空洞的故事——想像加密貨幣在未來將接掌全球貨幣系統。像流行小說一樣,比特幣現象結合了幾個經久不衰的敘事——自由意志主義者想像一個沒有國家干預的世界,神奇科技的力量,以及「創造貨幣」的謎。
經濟學家與極端不確定性
社會學家的公共角色是提供必要的資訊,讓必須在極端不確定下行動的政治人物、公務員、企業家與一般家庭能夠做決策。為了達成這個使命,社會學家可以藉由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來從旁協助,也就是提供一個連貫、可信的敘事,並建立決策的背景脈絡。這些敘事可能包括故事(文學虛構內容),或數字(由大資料集或小資料集建構,比如經濟的統計資料或社會調查結果),或模型(那些看似有精確解方的小世界描述)。在經濟學、商業、金融學中,這些類型的推理通常是相關的。
經濟學家無法告訴政策制定者該做什麼決定,但他們可以幫助政策制訂者思考問題,並提供相關的資訊。社會學家的敘事就像專業從業者的敘事——例如醫生的診斷、工程師的專案說明、律師的案例陳述。相關敘事的挑選取決於問題與情境脈絡而定,所以小說、數字、模型的選擇,需要針對問題與情境脈絡進行判斷。我們試圖建構的敘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只有實用或不實用的區別。 在挑選敘事時,判斷需要兼容並蓄且務實去華。身為經濟學家,我們既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派,也不是新凱因斯學派或奧地利經濟學派、社會主義派、行為學派。但是,如果這些思想學派能在特定問題的情境脈絡中提供相關的見解,我們願意採納任一或所有的學派。有些學派聲稱他們根據一種對世界的通用先驗主張,為問題提供廣泛的答案——我們對這種學派都抱持懷疑的態度。
疑團無法像謎題一樣解開。在疑團中推理需要承認疑團的模糊性,並充分化解模糊性好澄清思緒。然而,即使是擬定一個問題,也需要具備技巧與判斷力。這是經濟學家能做的最重要貢獻之一。首先必須擬定一個疑團(無論好壞)來幫助大家在極端不確定下做出必要的決定。擬定要從找出關鍵因素及組合相關資料開始做起,這需要應用這些因素過去如何互動的經驗,並評估它們未來可能如何互動。決策流程需要了解問題所在的廣泛情境脈絡,多數判斷需要傳達給他人,且實施時也需要他人的協助。
質疑敘事
在不確定性下做出成功的決策,是一個協作的流程。得出最佳解釋之後,應該讓那個解釋訴諸公評,並準備好在新的資訊出現時,改變指引的敘事。喜歡奉承的人所犯的錯誤(例如小布希規劃伊拉克戰爭,或雷曼執行長富爾德導致公司的毀滅),與不怕誠實批評的人所締造的成就(史隆打造出全球最成功的公司通用汽車,甘迺迪因應古巴導彈危機的挑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小布希政府中的共和黨思想家認為,在伊拉克迅速建立證券交易所是穩定與民主的核心構件,但這是從先驗主張所構建出來的敘事,而不是因為他們對伊拉克的政治與文化有具體的了解。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來自「通泛」的解釋、意識形態、宏大理論,或根據抽象推理的形式公理所衍生的刺蝟敘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得面對獨特的情況,需要多元化的方法與模型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