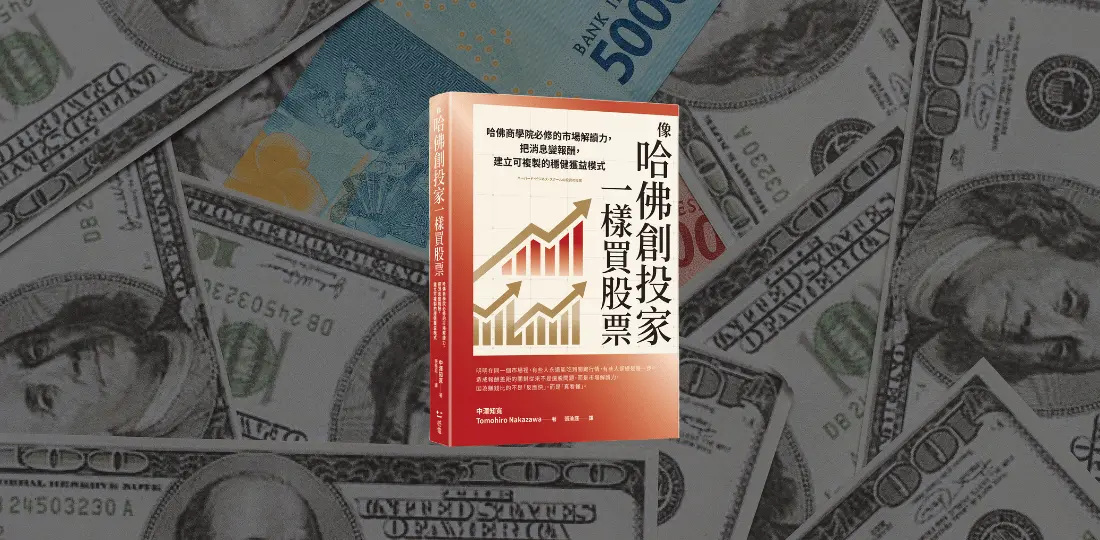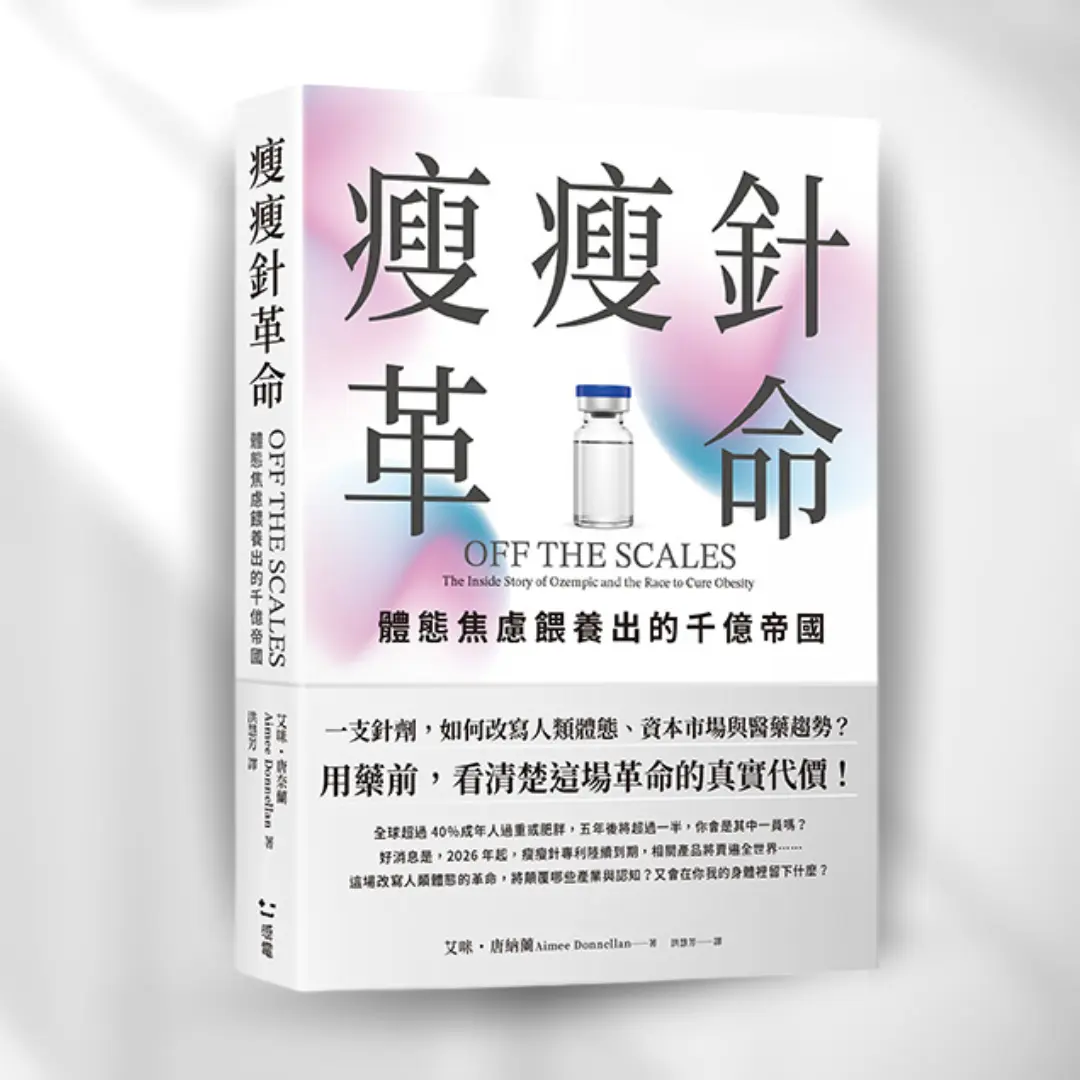蕭伯樂看起來似乎相當震驚。他甚至沒有反駁齊普拉斯的說詞,也代表這完全符合他對於梅克爾態度的理解。他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雙肩下垂,原本歡愉的情緒已不復見。他不斷地聳肩對我說,依照目前的發展,他想不出其他的解方。他似乎無話可說,只能不斷重複說著「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眼前的僵局,況且他也缺乏「職權」,不可能背著機構和我協商留歐協議。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真正的無力感,不是興趣缺缺、也不是充滿犬儒式詭計。所以,我試著想要鼓舞他的士氣。
「看看窗外那些人,蕭伯樂,」我邊說邊指著窗外,說:「不要期待德拉吉或拉加德會去做對的事、避開災難、尋求解決方法。那些人從來就不是為了這些人投票。他們是為了你和我投票,希望我們能合作達成協議。他們授權我們找出解決方法,如果我們做不到,他們會責怪我們。」
蕭伯樂刻意避開我的眼神。事實上,他整個人看起來確實不太好。
「我們的難題,」我繼續說:「我們的任務是找到解決方法,盡量降低在你我都承認已無法切割的雙重限制下所承受的痛苦:第一,〈備忘錄〉無法為希臘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第二,你我均未獲得授權討論希臘脫歐的事情。所以,我們應該在現有的限制條件下,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這是民選政治人物該做的事。」
「會是什麼樣的解決方案?」他問,這樣正好給了我機會,提出我們的替代方案。我應該好好把握,和他共同協商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接著我開始解釋,如何進行債務交換,好讓他能說服德國國會通過法案;如何讓希臘未來不再需要新資金;我們如何保證雅典不會再次陷入基本財政赤字的恥辱;如何擬定我們兩人都認同的大規模改革專案;我會如何與那些和德國總理以及部長關係密切的德國顧問合作擬定一系列方案,並依據這些方案成立投資銀行。簡而言之,我是根據修訂版的〈政策架構〉報告重新撰寫的一份摘要。過去一個月來,我們就是在忙著完成這份修訂版報告、補充新的想法,並換上新的標題:〈終結希臘危機:結構改革、投資導向成長與債務管理〉(Ending the Greek Crisis: Structural reforms, investment-led growth & debt management)。
我記得,當時蕭伯樂表示我的提案沒有任何問題。之後我又針對蕭伯樂的回應,尋求第二人的意見,我請高伯瑞寫下他的感想。關於蕭伯樂的反應,他的描述如下:
蕭伯樂非常專注地聆聽完長篇的報告,而且從他的肢體語言看來,他對於報告中的所有論點都表示認同。瓦魯法克斯不斷重複強調,解決方案必須具體而完整,而不是針對未來的失敗或是既有的紓困案做出評斷⋯⋯關於蕭伯樂的回應,最值得注意的一項事實是:他不斷聳肩,說他「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這件事。
我要求他提出回饋意見:「我在這裡請你,也就是歐洲地區最富有、最有權力的國家財政部長,告訴我應該怎麼做。你拒絕我的想法;你的總理又拒絕你的提議,同時間,我們總理的團隊與布魯塞爾小組的三巨頭代表進行的談判,並非朝著找出解決方案的方向走。所以,蕭伯樂,我到底該怎麼做?」
他第一次短暫地抬起頭來,冷淡地說:「簽訂〈備忘錄〉。」一切又回到原點。
「好吧,」我說:「假設我真的這麼做了。假設我簽了那份該死的文件。那麼請告訴我:在未來的六到十二個月內,我們的處境會變得不同嗎?結果將會是希臘再次面臨財政困難、希臘瀕臨崩潰邊緣的新聞標題隨處可見、希臘經濟陷入更嚴重的衰退,甚至在歐元集團內部引發政治風暴,不是嗎?」
此時蕭伯樂的表情有所緩和,他點頭表示同意,並說道:「這是為什麼我希望說服你們的總理,考慮退出歐元區。」
「但是你們的總理拒絕討論這個選項,」我說。
「好吧,那麼你們只能簽訂〈備忘錄〉。」他說,我們又再次退回到無解的狀態。
我心想,除了理性的論述,唯有訴諸人性,才有可能打破眼前的惡性循環。「蕭伯樂,能幫個忙嗎?」我謙虛地問。他親切地點頭。「這份工作你已經做了四十年,」我說:「但是我才做了五個月。從我們之前的會面你就知道,自一九八○年代開始,我一直都有仔細閱讀你的文章和演講內容。我希望你暫時忘記我們兩人的部長身分,我想要聽聽你的建議。不要告訴我該做什麼,而是提供建議。你願意為我做這件事嗎?」
蕭伯樂的副手們緊盯著他,他又再次點頭。我衷心地感謝他,希望他以一位年長的發言人、而非執行官員的身分提供意見。「要是你身處我的位置,你會簽下〈備忘錄〉嗎?」我原本以為,他會說出可想而知的答案(在當下的情況,其實也沒有多餘選擇)、以及一如往常的空洞論述。但是他沒有。相反地,他望向窗外。依照柏林的標準,當天是個炎熱晴朗的日子。然後他轉身,說出了出乎我意料的回答:「身為一位愛國者,我不會簽名。這對你的人民是不利的。」
我終於看到了可以突破的裂口,自然是想要用力敲開它。我說,既然現在我們都同意〈備忘錄〉「不利」,希臘脫歐也已不在談判選項內,那麼像是我提出的協議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這份協議完全符合德國和希臘人民賦予我們的職權和責任。但是,這時候的蕭伯樂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亡命之徒。
憤世嫉俗的人必定會說,蕭伯樂正在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競賽——正如同他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上澈底激怒薩潘的那番話,以及在五月十一日的歐元集團會議召開之前對我說的話,他希望利用希臘脫歐達成自身的願景:建立更小規模、更有紀律的歐元區,三巨頭堅守巴黎。這群憤世嫉俗的人所抱持的想法大致上是對的。但這並非事實的全貌。在我離開的當天,在我身後留下的並非一位信奉馬基維利的獨裁者,我留下的是一顆破碎的心,這個男人雖然在歐洲擁有無人能及的權力,卻無力去做他認為真正對的事情。正如同悲劇作家告訴我們的,最大的不幸莫過於掌握無上的權力、卻感到全然的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