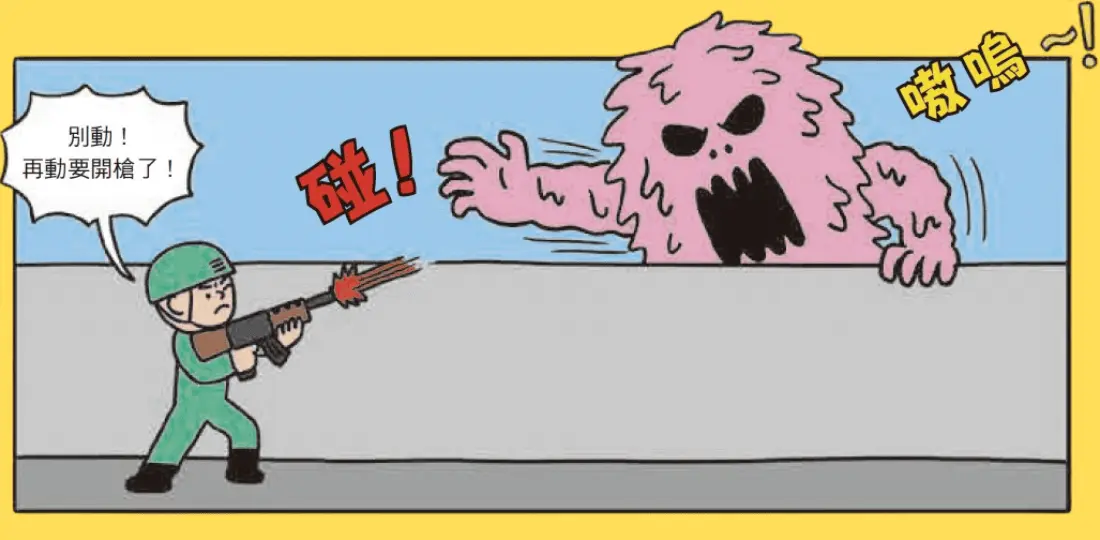回溯到幾世紀前至今,俗稱「四大」的德勤(Deloitte)、安永(EY)、畢馬威(KPMG)和普華永道(PwC)有著一段精彩輝煌的歷史。一則則積累財富、權力與運氣的故事,更是打動人心。事實上,我們現在如何工作、如何管理、如何投資,以及如何治理等等各種生活的層面,都深受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影響。
在這個看似有些枯燥、而且聲名狼藉的領域,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就像天之驕子,也是會計界最輝煌的成功案例。二○一一年,他們的總營收引人注目地突破一千億美元大關。自此之後數字更是持續攀升,並於二○一六年突破一千三百億美元,約全球排名三十。在普華永道於二○一七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惹出那場烏龍之前,該公司與迪士尼、Nike與樂高共同入選全球十大「最具影響力」品牌。
寡頭遊戲
倘若我們將在全球擁有近一百萬名員工(不含外包)的四大視為一體,無庸置疑,四大絕對是世界上最卓越的雇主之一。他們直接雇用的員工人數,比俄羅斯軍方的現役軍人還要多。要是把曾在四大工作過的員工也計算進去,更是數不勝數。四大過去的員工們,有些進入其他專業服務公司,有些則成為業界、政府部門的資深要角。部分前員工完全遵照「四大作風」行事,有些則是反其道而行。
四大主宰了會計、稅務和審計服務等關鍵市場。舉例來說,幾乎所有英美大型企業的審計業務,都是交給四大其一或多間進行。二○一七年的資料指出,標準普爾五百指數(S&P 500)的五百間公司中,有四百九十七間雇用四大來做審計,這些公司也幾乎買了四大提供的管理諮商服務。當年光是普華永道,就為《財星》(Fortune)五百大企業之中的四百二十二間公司提供服務。看來,倘若沒有四大提供的會計、審計和管理顧問服務,現代經濟體系將窒礙難行。
審計的魔力光環
四大企圖將自己在審計與會計方面的品牌資產,轉移到如策略、IT 諮商或不動產顧問等其他領域和服務。這麼做確實很有效:指派審計員能讓客戶在尋求建議的同時感到放心。利用審計的魔力光環,四大輕而易舉地贏得顧問方面的業務。然而,這些業務卻在許多層面上和原有服務產生利益衝突;此外,顧問業務的增長也極有可能提高風險,並損害企業的品牌形象。
而品牌削弱的情況,在稅務諮商方面更為嚴重。少數幾個重大稅務服務很有可能徹底摧毀四大的品牌價值。比起提升企業在誠信方面的聲譽,協助富人與跨國企業轉移收入或隱匿海外資產的舉動,只會腐蝕既有的好名聲。
期望落差
曾經擔任安達信律師的吉姆.皮特森(Jim Perterson)認為,在當代的審計標準下,一份無保留意見的審計意見,指的不過是審理的財務報表內容「大致上、且就我們所看到的多數時間上,沒什麼大問題。」會計專業人士是如此定義審計的,一份任何人都不可能出錯的工作。隨著時間過去,企業審計開始縮窄規模,結論也變得更有所保留。審計員漸漸開始只抽樣檢查交易,並以有限的方式進行控制測試。結果和結論則充滿但書。
期望落差似乎是一個處處可見的現象。原則上,病患會預期醫生可以治癒所有病痛;客戶希望律師能打贏每場官司。但當我們Google「期望落差」時,會發現這個概念絕大多數都是針對審計。基本上,其他職業和產業不太會受這種落差折磨。此外,透過Google 的搜尋結果,我們還可以發現受期望落差折磨最深的是審計員,而不是那些抱持著煩人期望的非審計員。
創造信任的技巧
麥克.包爾(Michael Power)稱審計為「創造信任的技巧」,讓投資者與大眾確信公司的管理階層是負責且廉潔的。法蘭辛.麥坎納(Francine McKenna)認為,「會計師事務所與成千上百名的審計員,應該是投資者的第一道獨立防線。」弗德列克.惠尼曾於一八九四年對伯明罕註冊會計師學生協會(Birmingham Chartered Accountants Students Society)表示,審計員的義務是「確認數字是否為真」。世人的普遍認知是無保留審計意見等於一間公司的會計帳通過審核;而審計報告則會針對該公司事務給予「真實且公正」的評論。
然而多數時候,當代負責上市公司審計的審計員,總是試著減輕眾人對於審計結果能保證程度的期待。舉例來說,審計員會強調他們不「保證」財務報表是正確的,他們只針對報表是否符合標準,以及就報表有沒有刻意誤導之嫌表示意見。在〈昏昏欲睡的看門狗〉(The Dozy Watchdogs)一文中,《經濟學人》的編輯發現美國當代的審計對於正確性並不發表任何意見,只不過是提供一份「單頁的通過/未通過樣板報告」,並針對公司報表內容在素材上是否合理呈現、有沒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給予「適當的擔保」。
儘管如此,預期落差仍舊存在。其中有兩個層面格外明顯。第一:審計員是否該警告投資者破產即將發生?第二:審計員是否應該察覺受審方的詐欺行為?
出賣靈魂
四大每年用避稅計劃讓政府與納稅人損失超過一兆美元的掠奪行為遭世人唾棄,他們卻仍樂此不疲地「從政府口袋裡掏錢」。在一篇刊登於《衛報》上的社論中,普林.西卡教授指出這些事務所「製造虛假交易、損失和不存在的資產,幫助客戶逃稅。」
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現代史,是一段從專業價值轉移到商業價值的故事。而這種轉移在稅務諮商方面的展現更是赤裸。推銷避稅手段的高峰期,正巧與會計師事務所商業化高峰期重疊。四大在稅務服務做出了埃德溫.華特豪斯想都想不到的事:用聲譽來換取金錢。在其中一個案例中,德勤被指控為客戶做出來的稅後損失會計建議罔顧公眾利益。然而德勤的品管聲稱,稅務顧問必須優先考量客戶的利益,而不是公眾的利益。稅務是四大出賣靈魂最為明顯的所在。
他們來,他們見,他們征服——在中國的的挫敗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WTO),四大終於能和國營合資的企業夥伴分道揚鑣。吉利斯提到,這樣的決定為四大開啟新的契機並點燃他們的野心。很快地,他們成長為超過四千名員工的大型企業,並「開始談著在不遠的將來,四大在中國的加盟所可與美國匹敵,成為全球網絡中最龐大的勢力」。最初將重心放在協助中國境內外資企業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很快地將收入重心轉移到中國企業身上。
中國明白對市場經濟而言,西方的會計方法是必要手段。一九九○年代,中國財政部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讓德勤與普華永道協助中國建立會計準則,並讓教育和監管機關的框架能與國際標準接軌。到了二○○六年,中國廣泛採用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獨霸一方
有些中國的地方部門選擇公開與四大為敵。迎擊外國企業入侵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市場上直接面對面。創造出中國四大(或一大、十大)這個的想法,深深誘惑著中國的會計監管機關。在一九九○年代,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為中國會計專業範疇的主要監管機關,會長丁平准深信,中國必須培植一家規模大到足以和外國「巨頭」匹敵的本土企業,丁平准稱之「一大」(Big One)。普華和永道的合併,讓丁平准有機會實現自己的計劃。
藉由這個合併,丁平准預見中國企業將能「團結起來,獨霸一方,和國外『巨頭』一爭高下。」而這個提案早有不少先例,中國政府曾在各個產業領域像是汽車製造業、電子業和重型機械製造業等,資助數間本地企業的合併。然而丁平准的計劃,卻遭遇了海內外的強力阻撓。他被擊敗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此事時仍深感遺憾:「就這樣,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被普華永道吞併了。在他們的文化入侵下,我們的夢想因此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