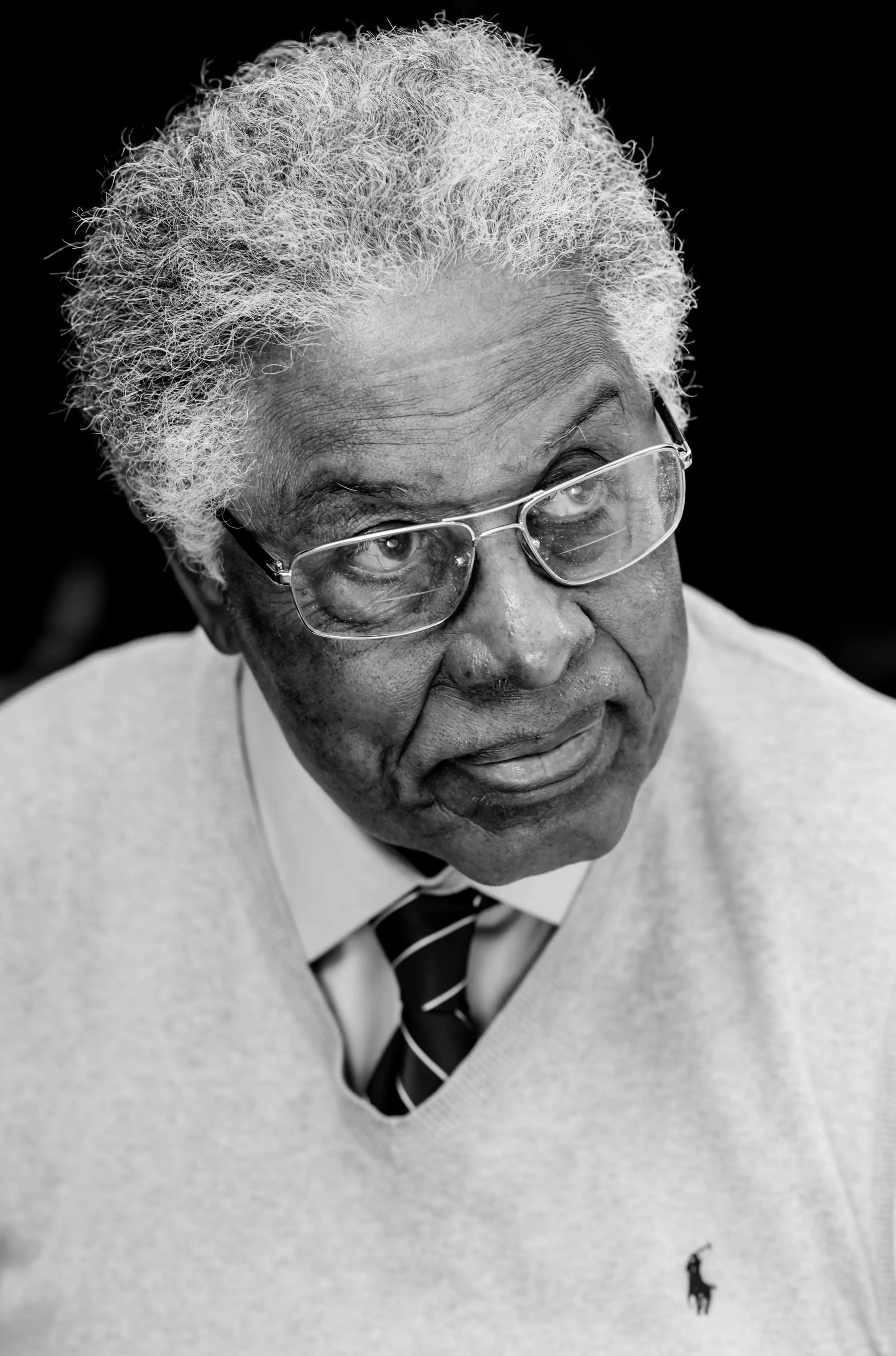許多社會正義文獻中,包括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教授的經典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眾人根據道德立場的合宜性建議各種政策,但往往很少、或根本不關注這些政策實務上是否可行、能否產生想要的最終成果。例如,羅爾斯在許多地方提到「社會」應該「安排」的事物,但並沒有具體說明安排的中介工具或可行性。
棋子悖論
很難想像除了政府,還有什麼機構能夠承擔如此重任。但是,這又會回過頭來引發世人質疑把更多權力放到執政者手中的危險。那些危險不容「安排」這個聽起來純真無邪的字眼所掩蓋。室內裝潢師的擺設是「安排」(arrange),政府的擺設是「規定」(compel)——兩者之間的差異絕對稱不上細微。
政府必須強制執行一些規定,從交通法到反謀殺法,應有盡有。但是這並不表示,為了實現任何看似合宜的事物而擴大政府的強制力時,不需考量任何危險。那可能代表為了某個有影響力的人口群體所熱衷的聖戰,而摧毀每個人的自由。
羅爾斯的這個觀點絕非他一人獨有,甚至不是現代才出現,十八世紀就已經有人具備類似的思想。亞當.斯密便提出反對,也對教條主義理論家的自以為是不以為然——套用他的話來說,這些「制度人……似乎想像他們可以像在棋盤上擺設棋子一樣動動手指頭,就能輕鬆安排廣大社會裡的各個成員。」
亞當.斯密針對「合宜性的高估」以及對「可行性的忽視」所做出的批評,今日仍是社會正義願景基本謬誤的一個要素。它所隱含的意義擴及各種議題,從財富的重分配到所得統計數據的解釋,無一不及。
無論規模是中等還是全面,財富的沒收與重分配是社會正義議程的核心。雖然社會正義的倡議者強調他們眼中的政策合宜性,但是這些政策的可行性所受到的關注卻少得多,而嘗試和失敗的後果通常也幾乎沒人在乎。
毫無疑問,政府、甚至是市井盜賊,或多或少都能夠重新分配財富。不過,嘗試更全面、長久的沒收與重分配政策的實際結果,究竟是成就還是危害,才是更大的議題。道德問題暫且不論,這些最終都是事實面(factual)的問題,必須在實證證據的領域尋找答案,而不是在理論或修辭裡。
財富的重分配
儘管「富人」財富的沒收與重分配政治上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實際上能實踐多少,取決於「富人」有多麼像棋盤上的棋子般任人擺布而不會有任何反應。如果「富人」能預見重分配政策並做出反應,政策的實際成果可能將迥異於預期。
在絕對君主制度或極權獨裁的國家中,政府可以毫無預警地突擊,對經常被當做沒收對象的「百萬、億萬富翁」實施大規模的財富沒收。但是,在民選政府國家,沒收性課稅或其他形式的沒收規定在付諸法律落實之前,必須經過公開提案,隨著時間過去向選民爭取足夠的政治支持。如果那些「百萬、億萬富翁」對所有動靜不是漠不關心,就很難對即將臨頭的沒收和重分配政策全然無所知覺。我們也不能假設他們會像綿羊一樣,乖乖等著被剃毛。
當「富人」預警到財富將會被大規模沒收之際,他們可以選擇的其他出路,最明顯的有:(一)把財富投資於免稅的有價證券;(二)把財富移出稅收管轄地;或是(三)自己離開稅收管轄地。
在美國,稅收管轄地可能是城市、州或聯邦政府。各種避稅方式都可能會為「富人」帶來一些成本,如果他們的財富形式是不可移動的資產,像是鋼鐵廠或連鎖商店時,或許也難逃沒收的劫運。但是,如果是當今全世界各地全球化經濟體裡的流動資產,那麼他們只要點幾下滑鼠,大量的資金就能透過電子的方式,從一個國家轉移至另一個國家。
也就是說,在某個司法管轄區提高「富人」稅率的實際結果是一個事實面的問題。結果不一定可預測,潛在後果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讓沒收計劃可行。提高稅率X%無法保證稅收增加X%——結果甚至可能完全沒有增加。當我們從理論和辭令轉向著眼於史實,就可以檢驗社會正義願景外顯與內隱的假設。
價格控制的反應
正如人的行為會隨著政府改變稅率而變動,當政府改變其他交易條件時,人的行為也會隨之改變。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之一。這是經濟學家幾個世紀以來、甚至在還沒有所謂的經濟學家之前就有其他人明白的道理。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政府立法為各種商品和服務訂定價格,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甚至更早的古巴比倫時代。
受定價法規約束的人很少會保持被動,彷彿任人擺布的棋子。有多少政府在通過這類法律之前了解這一點,不得而知。但是眾所周知,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儘管完全明白價格管制的負面經濟後果,他還是決定實施這些管制。當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對此提出批評,尼克森的回應是:「我才不管傅利曼說什麼。他又不競選連任。」 事實上,尼克森總統確實是以比前次當選更高的票數連任,入主白宮。
至於價格管制對經濟的影響,與幾個世紀以來如此實行的其他地方和時代沒有兩樣。當政府訂定的價格低於供需均衡的水準時,消費者的需求量會因為人為壓低價格而上升,生產者的生產量也一樣會因為人為壓低價格而下降。消費者與生產者都不是被動的棋子。最終的結果就是食品、汽油與許多其他物品普遍短缺。但是,這些後果只有到選舉之後才會普遍清楚浮現。
這些現象都不是美國獨有。2007年,非洲辛巴威政府為了解決失控的通貨膨脹,下令大幅降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辛巴威人民「以欣喜若狂(且曇花一現)的購物瘋潮迎接大降價」。但是,就像在美國,這波消費者需求量的增加伴隨著生產商供應量的減少:
麵包、糖和辛巴威人的主食玉米麵都被搶購一空⋯⋯肉類幾乎不見蹤影,即使是中產階級在黑巿有錢也買不到⋯⋯醫院病患也因基本醫療用品缺乏而死亡。
非洲人也和歐洲人或美洲人一樣,都不是被動的棋子。
關於世界各國許多形式的價格管制,許多研究都揭露非常類似的模式。 這讓人不禁想問:「政客為什麼沒有從錯誤中學到教訓?」政客當然有學到教訓——他們學到什麼在政治上有效:從政治觀點來看,他們所做的事沒有錯,雖然這些政策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在政治上可能犯的錯誤,就是假設社會可以透過政府的「安排」來達成某個理想(包括社會正義),而不考慮政府機構內在的誘因與限制的形態。
最低工資法
不是所有的價格管制法規都是強迫降價,有些價格管制法規是強迫漲價——這時候,由於價格上漲,生產者會增加生產,但消費者會減少購買。還是一樣,不管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不是沒有反應的棋子。強迫降價的法規通常會造成短缺,而強制漲價的法規往往會產生滯銷的剩餘(surplus)。
以前者來說,租金管制就是一例,造成世界各地城市的住房短缺。 美國農產品價格援助計劃就屬於後者,導致農民的作物種植量高於消費者在人為抬高的價格下願意購買的量。產品滯銷,政府就要祭出成本高昂的計劃,採購並儲藏剩餘的產品,同時思考如何清理善後並設法限制未來的生產。這些成本耗費納稅人數十億美元。
最低工資法是強迫漲價的一種特殊形式,通常會得到社會正義願景的倡議者支持。最低工資法是普遍認為有利於窮人的眾多政府政策之一,它阻止窮人自己做決策,因為他們做的決策不如代理決策者透過政府權力強制執行的決策。
然而,根據傳統的基礎經濟學,貴的東西人通常會少買。如果是這樣,那麼雇主(同樣不是沒有反應的棋子)面對最低工資法(價格較高)時的勞動雇用量,往往會低於供需決定的工資(價格較低)下的雇用量。在這裡,滯銷的剩餘稱為失業。
雖然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率通常低於一般勞工的工資水準,但往往高於新進菜鳥在自由競爭市場由供需所決定的工資。因此,最低工資法對年輕的初學者、特別是青少年勞工的影響往往更大,而這些群體的失業率與經濟原理的檢驗結果尤其吻合,顯示最低工資法會增加失業率。
如果察看各項現有的官方統計數據,這個主題的歧見似乎早就應該能夠化解才是。但是,多年來一直有人極盡巧思,規避最低工資法顯而易見的效應。那些已有其他文獻闡釋、檢驗的論述,本文不再贅述,只列舉出一些簡單明白的事實說明。